白衣如寄
姬汶在一个秋夜逃离了洛邑,那一天月光皎洁明亮,一点也不适合奔逃。
他最后遥遥看了一眼月光下古老的城池,乳白色的月光如水流泻在灰色的粗粝石块上,却并不能洗尽百年以来积压下的尘垢,姬汶曾不止一次梦见过,总有一天那些尘垢会压垮看似坚固的城墙,哗啦啦的倒塌的石头将这个国家的每一块苍老的血肉与骨骼都碾压掩埋。
他马不停蹄地奔逃出周国,这并不是难事,在他年少时,每每展开地图,总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找到蜷缩在魏韩之间的母国。
姬汶不知道在他拼了命地逃离自己的母国的时候,另一个人也正拼了命地逃回自己的母国,而他们极为巧合地都在魏国的大梁停下了脚步。
姬汶的第三匹马累死在前往大梁的山野小路上时,他随着马匹摔落在地上,映入眼帘的是“嘉鱼居”三字,随后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哥就急忙将他扶到简陋的木桌边坐着,还从井中汲了些水给他喝。
“嘉鱼居?”姬汶也顾不得什么祖宗之礼,咕嘟咕嘟喝下一大碗水,有些好笑地看着这招牌,自言自语道。
“这位公子可有意尝尝小店的飞龙在天?别看蔽店虽小,这飞龙在天可是远近闻名。“小哥这就卖力地说了起来,”公子可知道这飞龙在天的来历?当年我们魏国的大名士张仪在东都洛邑初试锋芒,便是用这道飞龙在天打动了如今的东周公,这才得以入秦,拜相封侯,成就了一段佳话——”
姬汶自然是知道这些的,他知道那个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让山东六国恨得牙痒痒的士子,他和大部分人都觉得,那大概是个满口利齿,胡话连篇的无耻小人,只可恨如今的世道让这样的小人得志——不是不怨恨,也不是不羡慕,更不是不酸涩。
他的父亲就是羡慕和酸涩的那一个,也是在张仪洛邑初露锋芒这个故事里的一个陪衬。
“将鱼生比作乱世,举重若轻,嬉笑不羁,细想又准确精到,我曾见过不少名士,如张子那般的,少见。”他的父亲曾说起过与张仪在嘉鱼居初见的场景,“三分痞气,七分锐气,白衣落拓,自是名士风流。”
姬汶对这样的评价嗤之以鼻,小人便是小人,何来风流?
然而他永远都记得他的父亲向他说起的他们鼎前问天的那一晚。
“敢问哪国青史愿存张仪啊?”
父亲微微眯起眼睛,随后喟叹一般,吐出一句沙哑悠长的“秦”。
仿佛姬汶真的看见了那个夜晚,两个青年高举的火把映照在他们闪闪发亮的双眸里,火光照亮了青年们兴奋而年轻的脸颊,照亮了九鼎繁复的花纹,照亮了洛邑灰暗的天,也照亮了整个天下。
“然而张仪身为魏国宫室之后,不为母国计,反替虎狼之秦擘划筹算,蚕食母国土地,小哥身为魏人,不应恨之入骨么?”姬汶点了份飞龙在天,与一壶魏酒,有一搭没一搭地与小哥说起话来。
小哥一时瞠目结舌,答不上话来,目光游移到隔壁桌旁一个须发灰白的白衣老人身上,那老人正自顾自地喝酒,衣着简单布料却精良,但掩不住身上一股沉沉暮气,此时看见小哥的神态,扬眉一笑,搭腔道:“天下百姓皆以强权者为英杰,张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天下做棋盘,列国为棋子,寻常百姓看来自然是了不得的大人物,至于士人游说各国,为他国奔走者众,早已被视作寻常。”
“礼乐崩坏矣。”姬汶道。
“那么公子为何狼狈至此,奔逃出国?”老人放下手中的酒碗,起身行礼,“姬汶公子。”
姬汶豁然起身,睁大了眼,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老人,“先生如何知晓我身份?”
“之前只有五成,如今已是十成把握了,公子。”老人揶揄一般地笑道,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公子请坐,也莫要惊惶,老夫并不是周室派来的追兵,不过若是公子非要顶着这张酷肖乃父的脸在六国晃悠,恐怕很快就要被抓回周室了。”
“先生是公父故人?”姬汶惊魂甫定,呷了口酒,这才定下心神。
老人点点头,从身上取下佩剑,双手递交给姬汶,“曾蒙东周公不弃,以剑相赠,如今还请公子替老夫还与东周公。”
姬汶拔剑,剑身通透锋锐,剑气森寒,“湛卢?!先生是张仪?”
“有劳公子了,东周公知遇之恩,张仪没齿难忘。”张仪冲着姬汶又是一揖。
“先生何不亲去洛邑还剑?”姬汶道。
张仪看了一会姬汶,待到姬汶被他盯得发毛的时候忽然偏过了头,望着这漫漫山林,笑了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姬汶只能看见皱纹顺着他的眼角一道一道地刻下来,却看不见他眼中的神色。
他说:“张仪已不是当年的张仪了。”
一路上姬汶虽不免仓皇,仍听说了些市井传言,秦国新王即位后,朝堂上下皆不容张仪,甚至有人雇佣死士星夜于相府刺杀他,最后这位权势泼天的大秦相国终于是一路逃窜回了母国,虽仍被委以高位,然而个中滋味,虽说唯有张仪才能尽尝,姬汶也不是不能体味其中一二。
最后姬汶与张仪拼桌一醉,姬汶醉的不省人事,只听见张仪一直絮絮叨叨地说,说这天下大事,说这陈年琐事,聊自己,聊故人。
张仪说:“我曾经那么想要逃离这个国家,最后还是回到了这里。”
张仪说:“来时行单,去时影只,世道如此,悲夫张仪。”
张仪说:“张仪何其有幸,得遇明君以展胸中抱负,与秦王共同指点这山河万里。”
姬汶迷迷糊糊地笑了,“先生醉得胡言乱语了,说话竟也颠三倒四,如何能够不幸而又有幸呢?”
“幸与不幸,张仪不悔。”
姬汶最后趴在桌上睡着了,好像记得半梦半醒间张仪仍在说些什么,似乎还夹杂着咳嗽声,眼缝里好像还看见了一片鲜红,一觉醒来,已是身在大梁的一家客店之中了。
最后姬汶在魏国逗留了数月,还是回到了洛邑,当他把湛卢交还给父亲时,张仪的死讯已经在天下传开了,他苍老了许多的父亲看着剑身上的倒影,低哑地喃喃,“张子啊张子,你将百世垂名,我却只能为微末注脚。”
姬汶听说他的父亲在听闻张仪死讯的那一日醉倒在九鼎前,手边的火把早已燃尽,回到洛邑的晚上,他举着火把一一照亮九鼎,仿佛听见那个一身白衣的士子放声大笑,与他记忆里的苍老不同的,有力的,张狂的呼喊:”张仪二字千百年后青史永存!“
这年轻的,锋锐的白衣何其短暂,不过短短二十年光景,他的主人曾不无苦涩地同他说:”张仪已经不是当年的张仪了。“这年轻的,锋锐的白衣又何其悠长,千百年来多少士子前赴后继,不过为了一场指点江山的大梦。
——这指点江山的一场大梦啊。
——这让世间无数人都为之沉醉为之狂热的一场大梦啊。梦醒了,才知道梦的尽头不过是一片荒凉的荆棘地。
然而他说不悔。
幸与不幸,张仪不悔。
一年后,周天子亡,年轻勇武的秦王率大军开进了洛邑,虽然为逞一时之勇秦王嬴荡吐血而亡,然而九鼎终于是被秦国收入了彀中,八十余岁高龄的父亲聚兵反秦。
姬汶知道他的父亲再也不能高举着火把在星夜照亮九鼎的纹路了,然而那火种和九鼎却留在了许许多多的人的心里。
或许不过是星星之火,转瞬即灭,或许可以成燎原之势。
幸与不幸,皆不后悔。
THE END
姬汶在一个秋夜逃离了洛邑,那一天月光皎洁明亮,一点也不适合奔逃。
他最后遥遥看了一眼月光下古老的城池,乳白色的月光如水流泻在灰色的粗粝石块上,却并不能洗尽百年以来积压下的尘垢,姬汶曾不止一次梦见过,总有一天那些尘垢会压垮看似坚固的城墙,哗啦啦的倒塌的石头将这个国家的每一块苍老的血肉与骨骼都碾压掩埋。
他马不停蹄地奔逃出周国,这并不是难事,在他年少时,每每展开地图,总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找到蜷缩在魏韩之间的母国。
姬汶不知道在他拼了命地逃离自己的母国的时候,另一个人也正拼了命地逃回自己的母国,而他们极为巧合地都在魏国的大梁停下了脚步。
姬汶的第三匹马累死在前往大梁的山野小路上时,他随着马匹摔落在地上,映入眼帘的是“嘉鱼居”三字,随后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哥就急忙将他扶到简陋的木桌边坐着,还从井中汲了些水给他喝。
“嘉鱼居?”姬汶也顾不得什么祖宗之礼,咕嘟咕嘟喝下一大碗水,有些好笑地看着这招牌,自言自语道。
“这位公子可有意尝尝小店的飞龙在天?别看蔽店虽小,这飞龙在天可是远近闻名。“小哥这就卖力地说了起来,”公子可知道这飞龙在天的来历?当年我们魏国的大名士张仪在东都洛邑初试锋芒,便是用这道飞龙在天打动了如今的东周公,这才得以入秦,拜相封侯,成就了一段佳话——”
姬汶自然是知道这些的,他知道那个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让山东六国恨得牙痒痒的士子,他和大部分人都觉得,那大概是个满口利齿,胡话连篇的无耻小人,只可恨如今的世道让这样的小人得志——不是不怨恨,也不是不羡慕,更不是不酸涩。
他的父亲就是羡慕和酸涩的那一个,也是在张仪洛邑初露锋芒这个故事里的一个陪衬。
“将鱼生比作乱世,举重若轻,嬉笑不羁,细想又准确精到,我曾见过不少名士,如张子那般的,少见。”他的父亲曾说起过与张仪在嘉鱼居初见的场景,“三分痞气,七分锐气,白衣落拓,自是名士风流。”
姬汶对这样的评价嗤之以鼻,小人便是小人,何来风流?
然而他永远都记得他的父亲向他说起的他们鼎前问天的那一晚。
“敢问哪国青史愿存张仪啊?”
父亲微微眯起眼睛,随后喟叹一般,吐出一句沙哑悠长的“秦”。
仿佛姬汶真的看见了那个夜晚,两个青年高举的火把映照在他们闪闪发亮的双眸里,火光照亮了青年们兴奋而年轻的脸颊,照亮了九鼎繁复的花纹,照亮了洛邑灰暗的天,也照亮了整个天下。
“然而张仪身为魏国宫室之后,不为母国计,反替虎狼之秦擘划筹算,蚕食母国土地,小哥身为魏人,不应恨之入骨么?”姬汶点了份飞龙在天,与一壶魏酒,有一搭没一搭地与小哥说起话来。
小哥一时瞠目结舌,答不上话来,目光游移到隔壁桌旁一个须发灰白的白衣老人身上,那老人正自顾自地喝酒,衣着简单布料却精良,但掩不住身上一股沉沉暮气,此时看见小哥的神态,扬眉一笑,搭腔道:“天下百姓皆以强权者为英杰,张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天下做棋盘,列国为棋子,寻常百姓看来自然是了不得的大人物,至于士人游说各国,为他国奔走者众,早已被视作寻常。”
“礼乐崩坏矣。”姬汶道。
“那么公子为何狼狈至此,奔逃出国?”老人放下手中的酒碗,起身行礼,“姬汶公子。”
姬汶豁然起身,睁大了眼,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老人,“先生如何知晓我身份?”
“之前只有五成,如今已是十成把握了,公子。”老人揶揄一般地笑道,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公子请坐,也莫要惊惶,老夫并不是周室派来的追兵,不过若是公子非要顶着这张酷肖乃父的脸在六国晃悠,恐怕很快就要被抓回周室了。”
“先生是公父故人?”姬汶惊魂甫定,呷了口酒,这才定下心神。
老人点点头,从身上取下佩剑,双手递交给姬汶,“曾蒙东周公不弃,以剑相赠,如今还请公子替老夫还与东周公。”
姬汶拔剑,剑身通透锋锐,剑气森寒,“湛卢?!先生是张仪?”
“有劳公子了,东周公知遇之恩,张仪没齿难忘。”张仪冲着姬汶又是一揖。
“先生何不亲去洛邑还剑?”姬汶道。
张仪看了一会姬汶,待到姬汶被他盯得发毛的时候忽然偏过了头,望着这漫漫山林,笑了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姬汶只能看见皱纹顺着他的眼角一道一道地刻下来,却看不见他眼中的神色。
他说:“张仪已不是当年的张仪了。”
一路上姬汶虽不免仓皇,仍听说了些市井传言,秦国新王即位后,朝堂上下皆不容张仪,甚至有人雇佣死士星夜于相府刺杀他,最后这位权势泼天的大秦相国终于是一路逃窜回了母国,虽仍被委以高位,然而个中滋味,虽说唯有张仪才能尽尝,姬汶也不是不能体味其中一二。
最后姬汶与张仪拼桌一醉,姬汶醉的不省人事,只听见张仪一直絮絮叨叨地说,说这天下大事,说这陈年琐事,聊自己,聊故人。
张仪说:“我曾经那么想要逃离这个国家,最后还是回到了这里。”
张仪说:“来时行单,去时影只,世道如此,悲夫张仪。”
张仪说:“张仪何其有幸,得遇明君以展胸中抱负,与秦王共同指点这山河万里。”
姬汶迷迷糊糊地笑了,“先生醉得胡言乱语了,说话竟也颠三倒四,如何能够不幸而又有幸呢?”
“幸与不幸,张仪不悔。”
姬汶最后趴在桌上睡着了,好像记得半梦半醒间张仪仍在说些什么,似乎还夹杂着咳嗽声,眼缝里好像还看见了一片鲜红,一觉醒来,已是身在大梁的一家客店之中了。
最后姬汶在魏国逗留了数月,还是回到了洛邑,当他把湛卢交还给父亲时,张仪的死讯已经在天下传开了,他苍老了许多的父亲看着剑身上的倒影,低哑地喃喃,“张子啊张子,你将百世垂名,我却只能为微末注脚。”
姬汶听说他的父亲在听闻张仪死讯的那一日醉倒在九鼎前,手边的火把早已燃尽,回到洛邑的晚上,他举着火把一一照亮九鼎,仿佛听见那个一身白衣的士子放声大笑,与他记忆里的苍老不同的,有力的,张狂的呼喊:”张仪二字千百年后青史永存!“
这年轻的,锋锐的白衣何其短暂,不过短短二十年光景,他的主人曾不无苦涩地同他说:”张仪已经不是当年的张仪了。“这年轻的,锋锐的白衣又何其悠长,千百年来多少士子前赴后继,不过为了一场指点江山的大梦。
——这指点江山的一场大梦啊。
——这让世间无数人都为之沉醉为之狂热的一场大梦啊。梦醒了,才知道梦的尽头不过是一片荒凉的荆棘地。
然而他说不悔。
幸与不幸,张仪不悔。
一年后,周天子亡,年轻勇武的秦王率大军开进了洛邑,虽然为逞一时之勇秦王嬴荡吐血而亡,然而九鼎终于是被秦国收入了彀中,八十余岁高龄的父亲聚兵反秦。
姬汶知道他的父亲再也不能高举着火把在星夜照亮九鼎的纹路了,然而那火种和九鼎却留在了许许多多的人的心里。
或许不过是星星之火,转瞬即灭,或许可以成燎原之势。
幸与不幸,皆不后悔。
THE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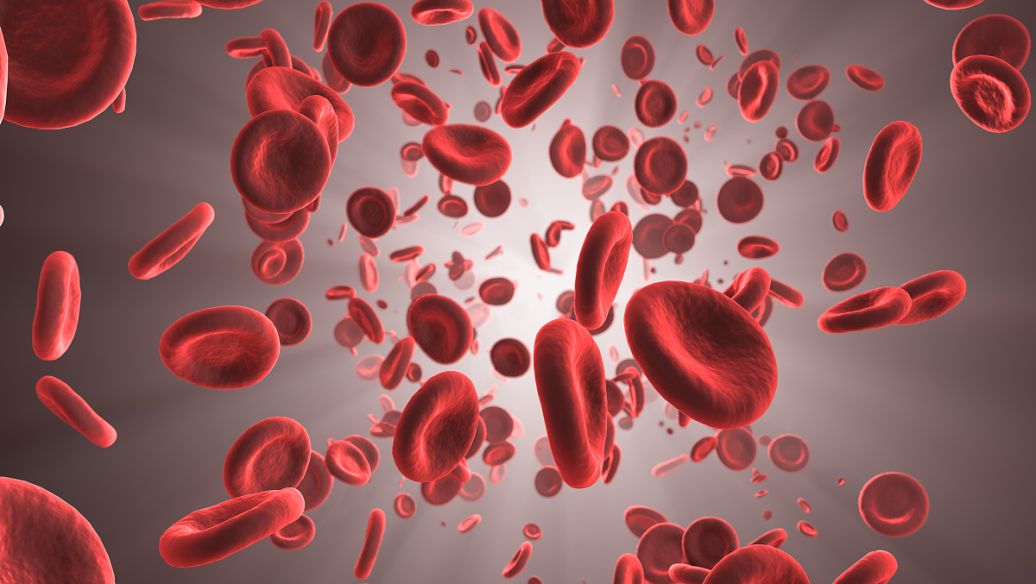


 果然我是个all党
果然我是个all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