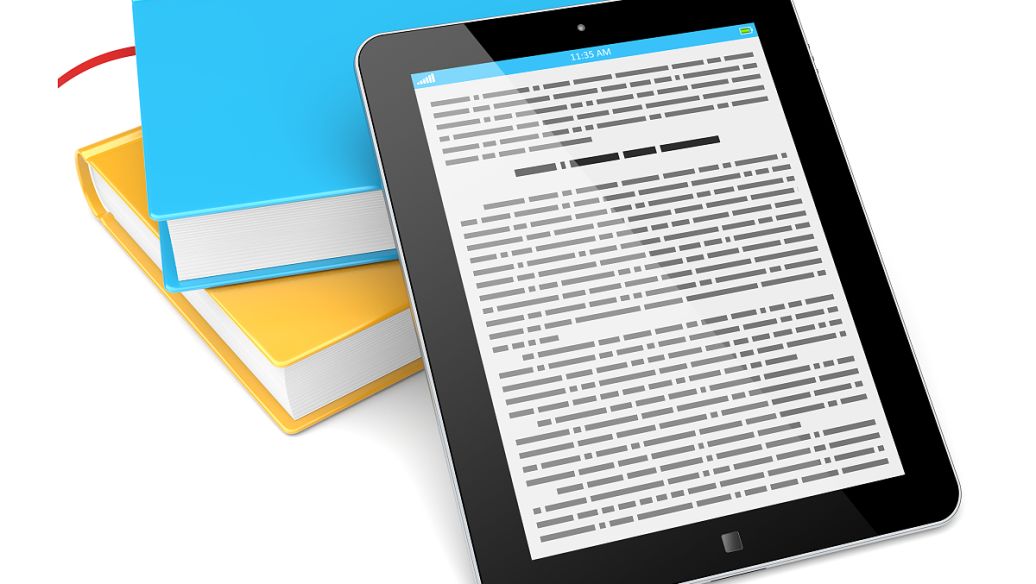皇帝是封建政权的全权代表,四大家族是封建政权的基干力量。《红楼梦》中对贾元春生活道路的描写,虽用墨不多,却巧妙地把四大家族与封建皇权捆到一起予以鞭挞,这就从政治上冲击了封建制度的要害。
贾元春“二十年来”的社会生活,由公侯小姐而宫廷女史,而凤藻宫尚书,直至贤德妃,到达了封建地主阶级妇女所能达到的最尊贵的地位。这是一条曾为封建主义的维护者薛宝钗一度神往而终不可及的生活道路。但作者却居然把她归入“薄命司”,在判词中把她与皇帝的关系比喻为兔子与猛虎的关系。否定这种生活道路,表现了曹对皇权的批判。
在贾元春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为贤德妃的消息传到贾府之前,贾府正在给贾政做生日,突然夏太监乘马而至,召贾政立刻入朝,致使“贾母等阖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地使人飞马来往探信。皇帝召见臣子本是正常现象,况且又预先说明是“在临敬殿陛见”,贾府却忐忑不安到这种程度。这就反映出当时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风云是何等地动荡不定,即便是象贾府这样的世代公侯之家,也存在着瞬息之间巢倾卵破的可能。贾元春当了皇帝的私人秘书和小老婆,这固然使贾府多了个政治靠山,但同时也给贾府带来了“登高必跌重”的危险。贾府之所以要多方拉拢夏太监之流流,也正是由于宫廷内部斗争的复杂尖锐。因此曲子里写贾元春死后还托梦给贾政夫妇,要他们急流勇退,及早抽身。这实际上是暗示贾府的被抄,乃是直接卷入了宫廷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结果。然而贾府要想维护其既得的家世利益,除了“勤劳王事”以外,别无他路可循。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贾府就是这样。也只能这样。故而在贾元春将以贵妃的身份回家省亲的消息传出以后,贾府的统治者们无不喜气盈腮,不分日夜地筹建“省亲别院”。而王熙凤在得意之余又以此为话题,与赵嬷嬷扯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就“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故事。说故事者或许无心,但作者则十分有意。“太祖皇帝仿舜巡”,目的是为了“震慑”各族人民,加强其反动的政治统治;当今皇帝让妃子们“归省”,目的是为了宣扬“孝”为“仁”之本,加强封建正统思想统治。贾府统治者们所以要用“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即便掏尽腰包也在所不惜,目的是为了借助皇权抬高自己的社会声望,以维护和扩大家世利益。在作者看来,贾府的当年“接驾”和眼下的“修盖省亲别院”,都不过是一种“虚热闹”。这就不仅是对四大家族的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的诅咒,也不仅是对四大家族已摯襟见肘、今不如昔的揭露,更为主要的是对皇帝及其后妃们借巡幸和省亲糜费资财的谴责,是对皇权尊严的嘲讽。
实际上所谓“皇恩重元妃省父母”,也是个名副其实的“虚热闹”。贾府不惜耗尽内囊,造了座“天上人间都具备”的大观园,这是何等隆重!圆中“处处灯火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这是何等欢腾!元妃“何处更衣,何处燕坐,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息”,皆先经太监审定,这是何等威严!然而,谁知迎来的却是个“心事满腹道不得、洋装欢笑掩啼痕”的“贤德妃”。正是生活的辩证法,教育了这位“贤德妃”,使她认为到那堂皇巍峨的“九重金阙”却原来是牢笼般的“不得见人的去处”,而黄袍加身的自己只不过是金丝笼中的小雀罢了。
还须指出的是,《恨无常》这首曲子里对贾元春的死反复咏叹,是有政治用意的。贾元春毕竟是贾氏宗族在最高统治集团中的政治靠山。不但那些“国舅老爷”们佁仗她的地位可以横行不法,就是那些京官朝臣、地方督抚们也都以“圣眷尚好”与否决定自己与贾府的亲疏态度。因此,元春的荣枯与贾氏家族的兴衰是息息相关的。故而她的死去,甚至并不是善终,就透露了四大家族政治生命即将结束,最后崩溃的局面已经到来。
贾元春作为皇妃,她在宫廷宫廷中虽有痛苦之感,乃至产生对田舍之家的向往,但这丝毫也不能改变她的政治身份。然而曲中却对她的“荣华正好”到“无常又到”的突然巨变,寄予很大的同情,并且对她托给贾政夫妇的梦,也不无共鸣。这又暴露了作者和他所批判的阶级之间的血肉联系。
贾元春“二十年来”的社会生活,由公侯小姐而宫廷女史,而凤藻宫尚书,直至贤德妃,到达了封建地主阶级妇女所能达到的最尊贵的地位。这是一条曾为封建主义的维护者薛宝钗一度神往而终不可及的生活道路。但作者却居然把她归入“薄命司”,在判词中把她与皇帝的关系比喻为兔子与猛虎的关系。否定这种生活道路,表现了曹对皇权的批判。
在贾元春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为贤德妃的消息传到贾府之前,贾府正在给贾政做生日,突然夏太监乘马而至,召贾政立刻入朝,致使“贾母等阖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地使人飞马来往探信。皇帝召见臣子本是正常现象,况且又预先说明是“在临敬殿陛见”,贾府却忐忑不安到这种程度。这就反映出当时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风云是何等地动荡不定,即便是象贾府这样的世代公侯之家,也存在着瞬息之间巢倾卵破的可能。贾元春当了皇帝的私人秘书和小老婆,这固然使贾府多了个政治靠山,但同时也给贾府带来了“登高必跌重”的危险。贾府之所以要多方拉拢夏太监之流流,也正是由于宫廷内部斗争的复杂尖锐。因此曲子里写贾元春死后还托梦给贾政夫妇,要他们急流勇退,及早抽身。这实际上是暗示贾府的被抄,乃是直接卷入了宫廷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结果。然而贾府要想维护其既得的家世利益,除了“勤劳王事”以外,别无他路可循。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贾府就是这样。也只能这样。故而在贾元春将以贵妃的身份回家省亲的消息传出以后,贾府的统治者们无不喜气盈腮,不分日夜地筹建“省亲别院”。而王熙凤在得意之余又以此为话题,与赵嬷嬷扯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就“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故事。说故事者或许无心,但作者则十分有意。“太祖皇帝仿舜巡”,目的是为了“震慑”各族人民,加强其反动的政治统治;当今皇帝让妃子们“归省”,目的是为了宣扬“孝”为“仁”之本,加强封建正统思想统治。贾府统治者们所以要用“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即便掏尽腰包也在所不惜,目的是为了借助皇权抬高自己的社会声望,以维护和扩大家世利益。在作者看来,贾府的当年“接驾”和眼下的“修盖省亲别院”,都不过是一种“虚热闹”。这就不仅是对四大家族的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的诅咒,也不仅是对四大家族已摯襟见肘、今不如昔的揭露,更为主要的是对皇帝及其后妃们借巡幸和省亲糜费资财的谴责,是对皇权尊严的嘲讽。
实际上所谓“皇恩重元妃省父母”,也是个名副其实的“虚热闹”。贾府不惜耗尽内囊,造了座“天上人间都具备”的大观园,这是何等隆重!圆中“处处灯火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这是何等欢腾!元妃“何处更衣,何处燕坐,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息”,皆先经太监审定,这是何等威严!然而,谁知迎来的却是个“心事满腹道不得、洋装欢笑掩啼痕”的“贤德妃”。正是生活的辩证法,教育了这位“贤德妃”,使她认为到那堂皇巍峨的“九重金阙”却原来是牢笼般的“不得见人的去处”,而黄袍加身的自己只不过是金丝笼中的小雀罢了。
还须指出的是,《恨无常》这首曲子里对贾元春的死反复咏叹,是有政治用意的。贾元春毕竟是贾氏宗族在最高统治集团中的政治靠山。不但那些“国舅老爷”们佁仗她的地位可以横行不法,就是那些京官朝臣、地方督抚们也都以“圣眷尚好”与否决定自己与贾府的亲疏态度。因此,元春的荣枯与贾氏家族的兴衰是息息相关的。故而她的死去,甚至并不是善终,就透露了四大家族政治生命即将结束,最后崩溃的局面已经到来。
贾元春作为皇妃,她在宫廷宫廷中虽有痛苦之感,乃至产生对田舍之家的向往,但这丝毫也不能改变她的政治身份。然而曲中却对她的“荣华正好”到“无常又到”的突然巨变,寄予很大的同情,并且对她托给贾政夫妇的梦,也不无共鸣。这又暴露了作者和他所批判的阶级之间的血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