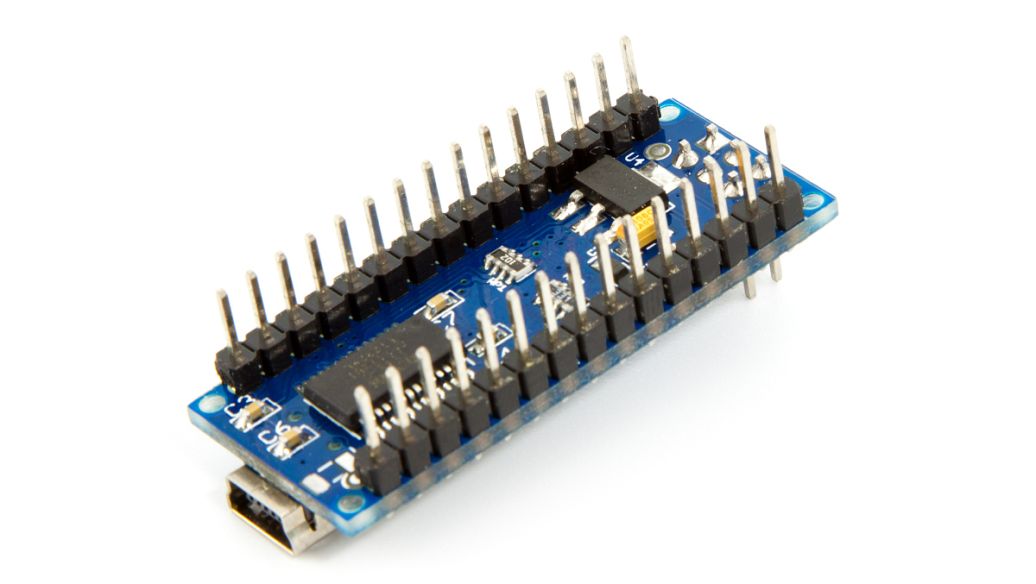起初我战斗只是为了保卫自己和我正在吃的食物,但后来我开始为战斗而战。我发现我在这该死的大楼里呆的时间越长,我就越生气。我无法在任何小马身上发泄我的愤怒,压力一直在增加,直到有一天我爆发了,真的伤害了一匹年轻的母马。那时候,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也失去了我的智慧。
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我开始从伤害别人中寻找解脱。起初只是小吵一架——扔两块钱,然后就打烊了——但后来就演变成了更激烈的争吵。我会接近那些弱者,把他们痛打一顿;让他们受苦,企图使我自己的痛苦变得迟钝。许多人试图逃离;我不会让他们逃跑,除非他们流血乞讨。那些反抗我的人遭受了更严重的打击。
有一天我在工厂的地板上杀了一匹小马。这是我第一次杀人。我清楚地记得战斗是如何进行的。我在工作状态我和另一个帕伽索斯一起把一些刚刚压缩过的光谱转移到保存室,她在什么东西上滑了一下,在过程中溅出了一大桶靛蓝;这种骚动肯定会让我成为下一个被砍断的人。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会因为一个愚蠢的错误而被杀,这一事实让我怒不可遏。
我那几周又几周的情绪压抑在一次爆炸性事件中爆发出来。当母马站起来说对不起时,我踢了她一脚。她向后一翻,在她的左翼上发出令人作呕的嘎吱声。当我走进去,开始用我的后蹄和前蹄反复击打她时,她对我的怜悯之声在我的耳朵里消失了。
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我开始从伤害别人中寻找解脱。起初只是小吵一架——扔两块钱,然后就打烊了——但后来就演变成了更激烈的争吵。我会接近那些弱者,把他们痛打一顿;让他们受苦,企图使我自己的痛苦变得迟钝。许多人试图逃离;我不会让他们逃跑,除非他们流血乞讨。那些反抗我的人遭受了更严重的打击。
有一天我在工厂的地板上杀了一匹小马。这是我第一次杀人。我清楚地记得战斗是如何进行的。我在工作状态我和另一个帕伽索斯一起把一些刚刚压缩过的光谱转移到保存室,她在什么东西上滑了一下,在过程中溅出了一大桶靛蓝;这种骚动肯定会让我成为下一个被砍断的人。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会因为一个愚蠢的错误而被杀,这一事实让我怒不可遏。
我那几周又几周的情绪压抑在一次爆炸性事件中爆发出来。当母马站起来说对不起时,我踢了她一脚。她向后一翻,在她的左翼上发出令人作呕的嘎吱声。当我走进去,开始用我的后蹄和前蹄反复击打她时,她对我的怜悯之声在我的耳朵里消失了。